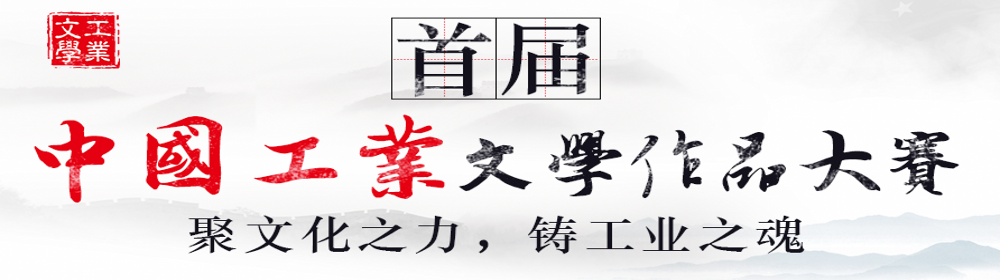“异相”中的人性及众生
刘云霞——读梅钰《十二个异相》2020-05-12 
阅读梅钰《十二个异相》的过程中,有个问题一直萦绕脑际:一名写作者应该运笔于何处?
有如此一问,是因为太多了这样的作品:没有时代印记,凌空于社会现实,文字花里胡哨,情节玄乎其玄,但掂一掂却轻如一堆泡沫;要么就是脸谱性人物走在公式化的情节里,或是媒体语的场景化,文学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根本无从谈起。
梅钰的笔在生活里。
医疗、教育、法律,婚姻、家庭、人生,壶口岸边的摆滩者,老街里的流浪儿,校园里迷茫的孩子,婚姻中情感错位的男女,一个个都是身边鲜活的存在。对这些鲜活人物的鲜活故事,她不是漠然的讲述者,更不是局外看客,而是置身其中的一员,用一颗感同身受的悲悯的心,在人性深处触摸,在社会厚土里开犁。
《大寒过后》,一个最底层家庭的故事。车祸致孩子成植物人,“大病”把一个家庭拖向深渊般无尽的煎熬。此种境况,是作者笔下的“这一个”,也是无数个遭遇此境的家庭的现状。围绕着孩子的拯救,家族、乡人、水滴筹中,看得见的众相纷呈,看不见的人心起伏爱心明灭都汇于笔下。
明线在写人的生死,暗线更在人性的拯救。
“拯救”是梅钰小说的魂灵所在。生命的拯救,家庭的拯救,心灵的拯救,时代的拯救……
《另一种真相》,一起貌似平常的情杀案。一波三折,似乎已经真相大白,继而又花明柳暗疑雾丛生,旋绕着的也是人性。在作者笔下,人性不是非黑即白,人生也不是一加一的简单算式,她以独有的细腻伸展着人性多元的触角,让人不觉中随行同进。
《红色曼陀罗》,围绕一个中学生被杀,展现了虚拟世界对现实生活的蚕食和侵蚀。原本是一个网络世界里的厮杀,一场无关现实的胜负,虚拟的刀却直取现实生活中的生命。
一群学生,在法律身边又远在法律之外的盲区;被教育包围又深陷教育的沙漠,被家庭无所不给的“爱”簇拥又处处被爱无视,教育的缺位,家庭的盲区,造就了一队精神沙化、情感冰点的人。文字中无不透出一种振聋发聩的声音:救救孩子!
值得一提的是,梅钰的律师身份,给她别开了一扇洞观人性和社会现实的窗,她的视窗里,是这样一种情形:
“他只将证据捏在手中,像捏着对方的命门……我是一个没有证据的女人,在爱情里断了所有退路。”
“她的爱情和婚姻不是模板,但却坐在高高的殿堂,要依自己的好恶给我们的婚姻判处死刑”。
“我想,…… 我们还有希望蕴育新生。结果法律让一个焦虑的女人代言,从她嘴里蹦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写着,快点快点!我想,她在追求结案率……”结案率,各种各样的率,同各种各样的量比一起,既影响我们又与我们无关。”
……
以上出自《异相》,一起不育离婚案的故事。烟火人间的冷暖飘落于法律纹路上,变成了冰冷机械的条款。相形之下,批判的力量油然显现。
作为一名真正的作家,文字的横竖撇捺不是无生命的砖瓦木石的堆砌,而是随处可以回放人间冷暖的家园。
梅钰的文字是她放飞的一个个小精灵。
甚至不用繁冗的叙述,每个文字都在生动地推着情节走。
《大寒过后》,女主人公兰英在得知儿子“被撞了”后,是这样一种焦急与慌乱:
“她跌跌撞撞,趔趔趄趄,让苍茫的黄河滩、苍茫的夏季暴雨前的一阵又一阵季风,和她眼里新生的白内障一起,浑浊了视线。”
“大风又旋回来了,之前一边倒的雨此刻急切得毫无章法,她越看越心慌,一刻也不能等,她拔开人群,插进错乱的风雨里……风也跑,雨也跑,她也跑……”。
《异相》中,写女主人公从法庭出来无以言喻的愤懑:
“雪花劈头盖脸,……它在愤怒,像拼尽全身力气呐喊,又像伸着千手千脚捶打。”
风卷沙漫雨急浪高,劈头盖脸的雪花,是景也是人的心,人的境;所谓情景交融,借景抒情都在其中了。在这样一种情境中,人不是人物,更像裹于景中的作者自己以及每一个握书在手的读者。借助文字的和弦,故事内外的情感得以高度共鸣。
在灵动的文字世界里,动词又总生动地雀跃于前:
主人公兰英在慌乱躲避风雨的人群中,“她把自己‘挤’进公厕里”,“她拨开人群,‘插’进错乱的风雨里……”(《大寒过后》)
“中画瘦成一张纸,轻飘飘‘铺’在床上……她‘拾’起他的手,细骨头上包一层松垮垮的皮……”(《影子在死神对面》)。
“挤”、“插”、“铺”、“拾”,一个动词拨动一个场景,省去许多无谓的陈述。
以虚驭实,以点托面,言尽意存,是梅钰小说一大特色。《影子在死神对面》中,李正的妹妹作为配角着墨很少,但每每也是不可忽略的精彩所在:
“门上破旧帘子,花色被阳光吸尽了,只留一条一条肮脏的印记,可妹妹像看她的前生今世一样看它。”
一条破旧帘子,“看”的一瞬间,似乎已经道尽一个既哑又病的女孩一生的不幸。
在《指尖花开》、《劝退》、《绑架》等关于婚姻家庭的故事中,作者凭着一份独有的细腻和独到的笔力,把原本落影般斑驳抽象的心理活动写得生动具象可触可感,在无形中吸引着读者步步入胜——
“他就像空气,从未离开,但从不深入;分明存在,又无影无形。你要拿一团空气,怎么办?”
“绝望像八只脚爬虫,在身体里沿走,一步在心,一步在脑,一步蚀骨,一步伤魂。”(《劝退》)
“画面总是分裂的。前一帧,他还粘着她,腻着她……后一帧,他却伸出四脚,掴她,踢她……她在上一帧与下一帧里,慢慢死去所有的思维。”(《指尖花开》)
结尾同样不落窠臼。梅钰小说结局,不强行“圆满”,也不刻意“悲剧”,由此让作品充满了张力和余韵。
“时间越想越快”,是《大寒过后》的落幕语,生命在“想”中复活,人性也在“想”中转暖。大寒过后是立春,一个既虚又实,既自然又社会的收尾,较之于惯常“包袱”式大结局,无疑是一抹新风。
刘云霞
- 前一则: 山西打造乡村振兴新引擎
- 后一则: 习近平在太原考察调研
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