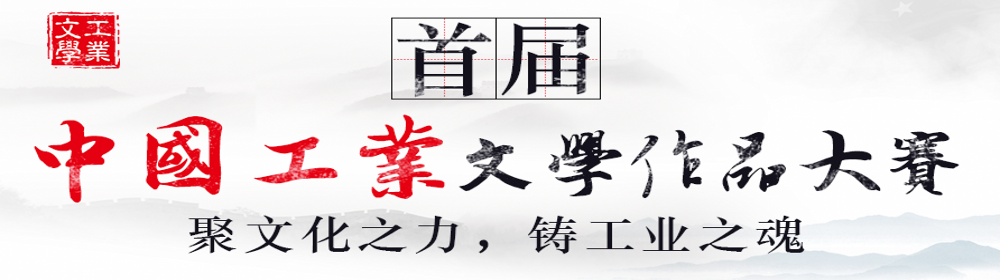夏尔西里(神州观览)
2019-02-18|
《 人民日报 》( 2019年02月16日 08 版) |
|
夏尔西里风光。 杨良其摄 |
 |
|
夏尔西里马鹿。 杨良其摄 |
 |
|
夏尔西里北山羊。 杨良其摄 |
 |
|
夏尔西里北山花。 杨良其摄 |
道路蜿蜒
我自认为足迹已遍布天山南北,对不同地域峻拔的山岭和妖娆的花草,都产生过经验可控的惊叹。可当摄影家老杨把一沓照片放在我桌前的时候,我还是被这纯净的画面震惊了。
无比湛蓝的天,像是被娴熟的油漆工一遍遍刷出来的,而几朵白云则更接近苏绣的点缀。紫色的花丛沿照片下端铺展开来,顺着山势绵延而上。远远望去,竟涌成了夕阳下大海的彩浪。“通透”成了被油画和苏绣联袂供养的词。让我更加愕然的是一张野生动物的图片,半山坡站满了上百只鹅喉羚,积木一样摆在那里,悠然自得,垂钓天色。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,就暗生欢喜,轻轻从舌尖上滑出,俨然自带着韵律——夏尔西里。
终于等到机会去拜会夏尔西里,那些相片,就像一张张滤网,内心顿然析出了干净而虔诚。
夏尔西里,蒙古语意为“金色的山梁”,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境内。集森林、草原、内陆湿地和荒漠等多种生态为一体。科研人员多次组织科考队,对保护区的地质、地貌和动植物资源进行考察,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动植物类型。包括珍稀兰科植物红门兰等在内的野生植物一千六百多种;包括雪豹、棕熊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在内的野生脊椎动物一百七十多种;昆虫四百多种。
从博乐市向北行驶四十里,折道向西。新修的国境公路平坦畅达,视野辽阔,这很容易让人放牧舒展的心情。窗外不时滑过的牛羊,像白云的倒影,远远望去,闲适而恬静。在博尔塔拉草原,白云的存在,是为了证明天的蔚蓝,而牛羊的移动,则是为了强调山的辽远。
进入山区,转过几道弯,在丛林叠嶂中,忽现一座营房。铁丝网、路障和持枪的士兵,让神采飞扬的思绪即刻着陆现实,已进入军事管理区。连队门前有一块面积不大的草坪,茂盛的绿草和摇曳的野花,让肃穆的军营平添了几分妩媚。更多的设施和房舍,被郁郁葱葱的云杉遮掩了。通往夏尔西里的道路,仿佛也被大山和林木收入了囊中,只是在车子驶近时,路才从山的怀抱里,挣脱出一截。车轮刚过,便稍纵即逝了。
开始爬山,道路变得凹凸不平。所谓的路,是在崇山峻岭中开凿一条狭长的石槽,通往山顶的瞭望哨,是进入夏尔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唯一道路。从连部的海拔一千五百米,到山顶的三千一百米,车子要在二十公里的山道上,盘旋攀升一千六百米的高度。一车多宽的砂石路,不时有石子被轮胎挤入山涧,半天才听到落地的回响。路的简陋和崎岖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安石的《游褒禅山记》:“夫夷以近,则游者众;险以远,则至者少。而世之奇伟、瑰怪,非常之观,常在于险远,而人之所罕至焉,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”感觉王半山千年之前,就为我们这次出行,备好了预言。
车子停在瞭望哨的板房前,这里已是整座山峰的最高点。一道铁门拦住车队,门右侧的铁丝网后,是哈萨克斯坦的边境。人车登记后,车头沿着平缓的砂石路慢慢下行,我们的呼吸和心境,都嗅到了夏尔西里与众不同的生态味道。
空中花园
宽阔的砂石路逶迤进草丛深处,将原本繁密茂盛的草甸切割开来。沿山坡而上的,是梯次分布的各类林木,娉娉婷婷的雪岭云杉,挺拔高峻的疣枝桦,粗壮开阔的密叶杨等组成混交林,遮天蔽日,一统天下。林木脚下,顺势倾洒出绿茵茵的草地,竞相开放着各色野花,雪青的糙苏、淡紫色的黄芪、紫红的红门兰、乳白的蔷薇、金黄的委陵菜都向天竞放,姿态万千,形色娇艳。雄伟的苍劲和阴柔的妩媚,在盘亘错节的回旋中,和谐调配,而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更像是一条细绳,试图捆扎住这幅巨型油画。
往里走,山势呈扇状,变得愈加平缓起来,这让更多的花草有足够的空间来排兵布阵,从山巅一直流泻到坡底。极目远眺,青山似乎是为了阻挡住这一汪碧绿才耸立在前方的。却未曾料到,最终自己也难逃被绿化的命运,成为绿的招牌,张贴在天边。起伏的群山被一床硕大的绿色棉被严丝合缝地覆盖着,这种映衬使得棉被之上的蓝天,像一幅刚刚抖开的绒布,纤毫未染,通透深邃。而白云则是画家才涂抹上去的颜料,甚至还没来得及洇开,就凝脂了。或许视觉习惯了荒漠和戈壁的赭黄,面对充盈的苍翠和碧绿,却忘记了所处的地域,竟有了置身南国丛林的幻境。幸而雄性的阿尔泰山脉,昭示着天山的品质,阻挡住向前奔涌的思绪。无论是相机的镜孔还是人的瞳孔,过滤如此纯美的画面,总易产生幻觉——眼前的画作,是人工的合成。毕竟,天然的造化,总会有些瑕疵,而眼前的美景,却无懈可击。
惊叹总是被缓慢行驶的车轮碾在身后,而新的欢呼又常常突然诞生。拐过一道山梁,整车人的目光一下就被眼前盛开的紫色花朵灼伤了。
简直就是一片燃烧正旺的紫色火焰,从山腰烧向坡底。脚下大地仿佛也被它点燃,变得沸腾而热烈起来。我们纷纷涌下车,举起相机和惊叹,靠近火焰。
路基下,是集中盛开的柳兰,一些黄芪和委陵菜夹杂其中,我还从没见过如此密度的花草,没有间隙、没有秩序,甚至没有起码的生存空间。一株挨一株,一棵挤一棵,每株花草都饱蘸激情,蜂拥而上,几乎撑破了我们的视线。花是有灵性的,把自己打造的如此璀璨,理应得到人类的惊叹的。这一刻,积攒了太久的美艳从土地深处、季节深处、思想深处迸发出来,让人们为自己才发现它而惊艳不已、愧疚不已。
走进鲜花丛中看似为了留影,其实是抵挡不住色彩的蛊惑。脚步是被花香牵引着,游进紫色的海水中,波浪很快就淹没了身影,只好拨开一人多高的花草,踮起脚尖,面对镜头,露出狂喜的笑脸。
抬头,一道铁丝网赫然出现,对面就是哈萨克斯坦。国家的概念不再抽象,变成了触手可摸的现实。一步天涯,莫过如此。陪同我们的领队说,咱们这边已经修了路,汽车巡逻。我们紧紧抓住铁丝网,生怕自己漏了出去。站在祖国土地的最边缘,我有了一种想哭的冲动。
动物王国
穿行在山间的谷底,路平缓笔直。羊茅、羽衣草、珠芽蓼拥围着更多不知名的野草,迫不及待地从山巅冲将下来,又被一道浅浅的车辙挡住去路。但草的清香却没能刹住,挤进车内,停留在嗅觉之上。于是,满车的青草味,弥散了视觉。那些挤在路边的花草,一簇绛紫、一簇明黄,我们的视线被装饰得五彩缤纷,车子也仿佛行驶在百花丛中。不时有被我们惊扰的粉蝶翩然飞起,华丽的双翅,引着仓促的目光追随进另一蓬艳花丛中。有两只彩蝶飞进车中,被我捉住一只,翅膀的尾部,长着一对类似于眼睛的图案,同车有熟知者说,这叫眼蝶,是在此生存的近百种蝴蝶中的一种。把蝶放在手心,仔细端详,它翅膀轻颤,两根触须不停转动,停留十几秒钟后,展开双翅,飞出车外。这只眼蝶一定是第一次感知了人类的温度,在它有生之年的记忆里,一定会有我的片段。想到这里,不禁哑然微笑,且暗自得意了。百种绚丽的蝴蝶,伴生百种鲜花的绽放,既是花的幸运,也是蝶的福祉。花是蝶的映照,蝶是花的延伸。
进入坦克沟,一条溪水从沟里流出,又被茂密的灌木掩盖,只能听到水声,无法看清真容。不少河曲柳和天山桦生长在河坝里,体形比灌木大很多。
“看,那是什么?”眼尖的人大喊起来,顺着手指方向,六七十米开外,两只动物在溪边喝水。车的出现,让低下的头抬了起来,并没有惊慌。车子停下,从包里掏出望远镜,看清楚是两只马鹿,雄鹿头顶着两蓬高昂的鹿角,将雌鹿掩在身后,与我们对望几眼,缓缓踱入林中。入林前,雌鹿还回望了一眼,神情若定。望远镜视线升高,更远的山梁,盘桓着更多的动物。几十只黄羊,在朝阳的山坡悠闲午餐。头羊站在高处,警惕地四处瞭望,弓形的两只羊角,像举起的两柄利剑。同伴争抢望远镜,轮流观赏。我们的到来似乎并未打扰动物的进食,无论马鹿还是黄羊,在它们目前的生存经验里,人类还没有构成威胁。
熟悉的山岗,一下就把摄影家老杨推了出来。他一定是刚翻过这道山梁,突然看见了四五十米开外那群吃草的鹅喉羚。我能想象得到他兴奋的状态,倏然跳下车,蹲站趴卧,抓拍几十张,直到羊群慵散地翻过山梁。那天,老杨指着照片,依然能感到他握惯了相机的手,因为激动而颤抖。他说,四十年前自己还是小伙子的时候,在牧区这么近距离拍摄过。
车子停在博尔得河桥头,河面有八九米宽,从茂密林间奔涌而出,水流湍急。河水清澈而冰凉,即使在骄阳七月,洗濯面颊,也有彻骨寒意。有人顺着河岸的草丛往里走,步行了几十米,领队大喊:不能再走了!要出国了!果然在河边,看见一个蓝色界桩,几乎被花草遮住,那是哈国的边界。大家调转方向,朝着河岸另一端,深入祖国腹地。刚进去,就见一男子慌张而出,大喊:野猪!这里有野猪!几个胆大的复返林中,果然见到了一片野猪新拱的草皮。
领队说,在夏尔西里碰见野生动物,是习以为常的事,再深入林子,会碰见雪豹、高鼻羚羊、棕熊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。这里还是黑琴鸡、环颈雉、石鸡以及许多鸟兽的天堂。
植物乐园
植物的茂密让路的性质越来越模糊,有些花草甚至与越野车比肩了。显然,草在这里生长是不需要节制的。纵情发挥,恣意奔放,无需顾忌身外的目光。在夏尔西里,每一株草都活成了它想要的样子。
东边晴空万里,西边一片乌云,衔来一阵雨。阳光下的水滴,晶莹剔透。在夏尔西里,撞见几只动物和邂逅一场雨一样,既毫无征兆又心不设防。
靠近一座小木屋,四周的蒿草已经将墙体遮掩,只顶出一小片屋盖。领队说这应该是上个世纪牧人留下的房子,这里已近百年没进人放牧了。木屋用一根根原木搭建而成,风吹雨淋,木质已朽,皲裂的深缝,几只黑蚁爬出。房间不足十平方米,屋角的炉灶已经坍塌,左侧的木炕锈蚀破败。透过小窗子,能看到新鲜的花草。想象百年前的某个清晨,一位年轻牧人点燃炉火,坐在炕头。看到第一缕阳光从高过窗棂草丛中透落,倾洒在他晾晒着野蘑菇的窗台上,他一定在思念心爱的姑娘,他要守住寂寞,坚持到秋天,卖掉肥壮的牛羊,迎娶新娘。如今,灶火虽灭,但草还在年复一年地生长,屋顶的一丛丛鹅冠草、马先蒿,迎风招展。有草的地方,爱情就不会枯萎。
离开木屋,车子一路上行,弯过一道坡,我们惊叹着眼前这一片灿灿的金黄。这是由多榔菊、风毛菊组成的菊花的海洋,每一朵黄花就是一支彩笔,将这半坡的颜色涂抹的整齐划一,心无旁骛。与紫色花海的奔涌而下相反,这些金色的烈焰顺势而上,一直烧到山顶,在阳光的助威下,演绎得轰轰烈烈。
有人发现路边的灌丛里,长满了野生草莓,颗粒如桑椹果大小,长在荆棘枝上。之前查阅了相关资料,知道这种植物叫树莓,果子酸甜鲜美,十分爽口。大家蜂拥采集,赞誉不绝。同时伴生的还有红果小檗、黄果山楂等浆果,成为舌尖的盛宴。夏尔西里丰富的植被,像家境殷实的富户,来了贵客随时都可以拿出美味珍馐款待。
夏尔西里,用一百年的生长,酝酿出惊世的模样。
来过之后,每个人都能感到,血液里有了新的重量。
《 人民日报 》( 2019年02月16日 08 版)
- 向前: 新春里奔跑的追梦人
- 向后: 聚焦总目标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


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