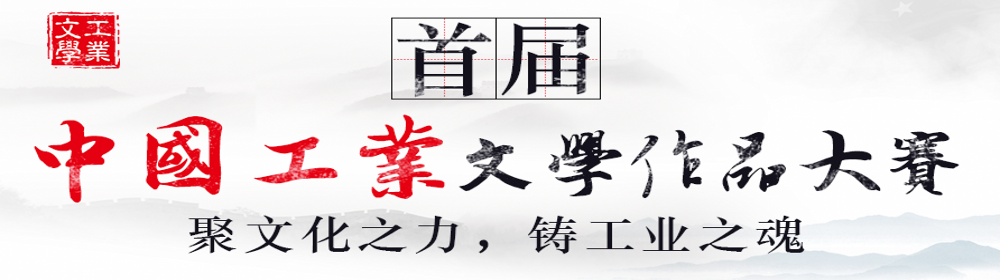唐德刚:胡适的“磁性人格”
2020-05-22 
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“磁性人格”( magnetic personality)这种性格实非我国文字里什么“平易近人”、“和蔼可亲”等形容词所能概括得了的。有这种禀赋的人,他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作用,恍如物理界带有磁性物体所发生的磁场。它在社会上所发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,端视其在社会中影响力之高低;影响力愈高,则幅度愈大。
这种磁性人格在古往今来的许多的大英雄、大豪杰,乃至诸子百家和宗教领袖,以及草莽英雄的性格之中都普遍存在。但是这种人与人间的吸引力却是与生俱来的,是一种秉赋;是一种“上帝的礼物”(gift from God)。它不是一个道德家(moralist)可以用修养功夫修养出来的。“修养功夫”深的道德家、哲学家或宗教家,他们可以为“圣”,为“贤”。但是“圣贤”可以引起社会上的“尊敬”,却不一定能讨人“欢喜”。
反之亦然。一个“掷果盈车”的梅兰芳、贾宝玉,或“天下 一人谭鑫培”,他能讨尽人间“欢喜”,却不一定能引起社会上普遍的“敬重”。能使社会上普遍的“敬”而“爱”之者,那就是胡适之这种具备有磁性人格,而他在社会上又无拳无勇,既不招忌,又不惹恨的传统社会里所产生的所谓“清流”了。
除去他这种先天秉赋之外,胡氏当然亦有其常人莫及的修养功夫。凭良心,胡适之该算是个真正当之无愧的“君子”了。他治学交友虽深具门户之见;但是他为人处世则断无害人之心。俗语说:“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。”如果当今世界上,人人都像胡适之,老实说,人类的“防人之心”也大可不必有了。我断不相信这个世界上,会有人为胡适之暗箭所伤的。
这一点,当然除了胡氏个人的秉赋和修养之外,他一辈子没有卷入过“害人”或“防人”的环境,实在也是维持他一生清白的最大原因之一。

再者,胡氏绝顶聪明,兴趣的范围广,欣赏(taste)的境界高。因而他在各行各业里所交游的都是些尖端人物。在这种情况之下,因而忌妒他的人也就不会太多。
金岳霖先生说:“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!”这就很明显的是一种“文人相轻”的心理在作祟。但是在中国哲学界里像金氏这种能够和胡氏“相轻”一下的“文人”也实在不多啊!在文学、史学、宗教……等各行各业上,其情形亦复如是。相轻者既鲜,剩下如我辈的芸芸众生就只有“爱而且慕”了。这也该是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所以能为举国上下一致接受的主要原因吧!
加以胡氏气味好,有所为,有所不为;深知自重,因而纵使“批胡”或“搞胡祸”的专家们也断难信口雌黄,骂胡适之“无聊”、“无耻”或“无行”。他们如果以三“无”中的任何一“无”来加诸胡适,也就会“不得人心”了。无聊、无行乃至无耻之人,在今日世界里,真是滔滔皆是!但是,凭良心,不是胡适!
笔者作此论断,深知师友中持反对意见者,亦大有人在。但是我们月旦时贤,却不可把任何历史性的人物,孤立起来加以分析。任何历史性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都是相对的。写历史的人不但要把受批评者的道德文章,与其他时贤互比;执笔者更应在人类所共有的七情五欲上,推己及人。如此则高山仰止,景行行止,我们对胡老师的公平评价,虽不中亦不远矣!

胡老师是有高度国际声望的人,因而他那人格上的“磁场”也就远及海外,五十年代初期,美-国颇具影响力的《展望杂志》(Look Magazine)推举出一百位当前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伟人,“胡适”大名亦荣列其中,为百人帮之一。但是这批推举者显然但知“胡适”其人,而不知“胡适”其事。因而他们推举的理由——“发明简体语文”——连胡适也不能接受!
“世界上哪有什么人能‘发明’一种文字呢?”胡先生笑着向我解释。
“仓颉!”我说。胡先生为之大笑。
我又问他,“既然他们对你的贡献并不太清楚,为什么偏把你选进去呢?”
“他们知道我的名字!”胡氏肯定地说。
知道“胡适”的名字就够了,贡献是必然的;贡献太多,不胜枚举。搞个“发明”出来,也就可代表一切了。
还有个洋人最耳熟能详的故事。
珍珠港事变前有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(Thomas Vernor Smith)当选众议员。胡氏因为与他有一饭之缘,得知其当选,乃柬请他来中国大使馆晚餐。孰知这位史议员,纱帽初戴,官常欠熟;他在华府下车伊始,手忙脚乱。餐会时间已近,他匆忙叫了部计程车,赶往赴宴,据说他在车上忽然想起,他还不知道主人的名字,乃询问计程车夫,车夫哪里知道。好在与“大使”吃饭并不要叫名字。满口“阁下”、“大使”……也就足够应付了。所以终席宾主尽欢。
宴会结束之时,“大使”送客,当然也免不了“欢迎到敝国旅游”一类的话了。
“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!” 史议-员肯定的说:“我到贵国观光,我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……大使先生,胡适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?”
大使闻言,笑颜大开。他回答史议员说,“胡适就站在你的对面啊!”
两人乃相拥大笑!
史议员既然连胡适做了驻华府大使也不知道,他显然对胡适在中国究竟搞了些啥名堂,也一无所知;既然对胡适博土一无所知,那他为什么到敝国观光,第一个就要拜会胡适博士呢?
这问题说穿了也无啥费解!
胡适之在纽约做寓公期间,好多人都笑他是纽约的中国“地保”。纽约又是世界旅游必经之地。途过纽约的中国名流、学者、官僚、政客、立、监、国大代……一定要到胡家登门拜访。过纽约未看到胡适,那就等于游西湖未看到“三潭印月”、“雷峰夕照”一样,西湖算是白游了。胡适之也就是纽约市的“三潭印月”、“雷峰夕照”……是纽约的八景之一。路过纽约的中国名流,如果未见到胡适,那回家去,真要妻不下织,嫂不为炊,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了!
加以胡适之生性好热闹,来者不拒,见者必谈。他又见闻广博,学富五车;任何小题目,都能谈得丝丝入扣。访客愈多,兴趣愈大。纵有些面目可憎,言语无味的客人,胡氏亦绝不慢客。所以他的纽约寓所,简直是个熊猫馆,终日“观光之客”不绝。施耐庵说:“吾友……毕来之日为少;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;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。”这个东郡施家,就颇像纽约的胡家。只是施家的客人是常客,胡家的客人是过路游客罢了。
胡适之的磁场,其吸引力是可惊的。片刻坐对,整日春风。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也就交游遍海内了。
抗战胜利后,戴雨农将军撞机身死,文人章士钊挽之以联曰:“誉满天下,谤满天下……”本来吃戴将军那行饭的人,誉满天下,谤亦随之,原是避免不了的。但是吃胡博士那行饭的人,就不同了,他虽然誉满天下,但是谤从何来呢?有英雄行径的人,总欢喜说“不招人忌是庸才!”吾人如把胡先生的“学问”和“事功”分开来算,就“事功”而言,胡老师原来就是个“庸才”啊!有谁又去“忌”他呢?
如果一个人,大德无亏,别人硬要批评他,那就只有观其细行了。吾人如观胡氏之细行,既然“无聊”二字亦不能加之于他;那么“无耻”、“无行”就更无胡适之份了。在这三无遍地的世界里,一个名满天下,而三无皆缺的书生,“我的朋友”之受人爱戴,也就不难理解的了。
史密斯议员虽然当面也不认识他,但是如果到中国观光,还是要慕名拜访,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?
本文节选自著名美籍华人学者、历史学家、传记文学家唐德刚先生(1920年8月23日-2009年10月26日)的《胡适杂忆》(华文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1990年2月第一次印刷)198——203页,题目为编者后加,图片来源于网络。
让我们跟随唐先生一起来认识一位有血有肉、多彩多姿、不是超人、不是完人、亦不是圣人,却是最近人情的人的胡适之。
- 前一则: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丨青春的颜色是什么?
- 后一则: 传承家国情怀积蓄前行力量
.jpg)